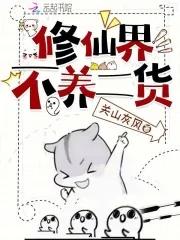書本網>王爺他總想太多 > 第86頁(第1頁)
第86頁(第1頁)
沈嬌翹着嘴角,收回手下了床。
衛鶴景終于能松一口氣。
然而還沒等他重新把衣襟掩好,小姑娘就從拔步床下的櫃子裡抱出來一個托盤放在了他身邊。
沈嬌坐回他身邊,攔住了他想要整理衣衫的手,向他介紹自己的計劃:“我本想着,這疤痕若是消不了,那我就給你做個刺青,這樣把疤痕蓋住。但是刺青和丹青雖說隻有一字之差,功夫卻天差地别。我對丹青頗有心得,對刺青卻是一竅不通。”
“不過這關系也不大。刺青一旦上了身,再想祛除可就是難如登天。倒不如我在夫君身上做丹青,若是效果不好、夫君不滿意,還可以時時調整。夫君要是想要變換圖案,那也十分方便。”
“我已經想好了一些設計圖案,保管能讓夫君開心。”
衛鶴景幾乎要氣笑了。
她這可真是思慮周全了,平日學習看書不見下了多少功夫,擺弄這些玩意倒是研究深刻。
小姑娘把托盤上的東西一一指給他看。
“這些筆都是我能找到的最柔軟的筆了。不會紮着夫君的。還有這些顔料。這些顔料也不是平日裡作畫的顔料,是我專門用妝匣裡各色胭脂水粉悉心調制的,顔色雖然不是很豐富,但是也夠用了。這種特質的水粉我之前在手腕上試過一遍,不容易蹭花,但是蘸水稍稍用力搓細還是很好卸除的。”
衛鶴景一眼望過去,托盤上的東西分門别類擺放得整整齊齊。
工具可真是夠“齊全”的。
沈嬌按住衛鶴景肌肉分明的胸腹,抄起一支毛筆蘸了調制好的水墨:“夫君躺好呀!我要開始了!”
衛鶴景攥了攥拳,最後還是自暴自棄一般依言躺平了。
但願這小姑娘能快些弄完,他可不确定自己能忍多久。
屋子裡依舊燃着燭火,拔步床的床幔還好好地束在床邊沒有放下來。燭光毫無阻攔地照射到床内。
權貴之家不像平民百姓那般節省燭火,一向是怎麼明亮怎麼來。
已經是晚上應該休息的時候了,屋内卻還燃着起碼十數支明亮的長燭。蠟燭的燭身幾乎都有成人手腕粗細,通體是清朗細膩的乳白,中間用工藝描出金光閃閃的各色花紋。
晉王府用的燭火從來沒有粗制濫造的。燃燒起來有煙的、嗆人的、聲音過大的,在最初的采選環節就不會進入考慮的名單。
但是再好的燭火也免不了偶爾炸一炸燭花。一聲“吡啵”之後,一滴乳白色微微透明的燭淚悄無聲息地滴落在黃銅托盤裡。
在這樣安逸的環境裡,沈嬌專心緻志地在夫君身上“揮毫潑墨”。
暖色的燭光照在男人飽滿的肌肉上,難得的朦胧而不油膩。
小姑娘已經換了三隻筆了。
顔料的來源是她的胭脂水粉,所以大多數的顔色都是偏紅的。但是小姑娘給夫君用的卻幾乎都是黑色和青色。
她喜歡明亮而鮮豔的顔色,可惜今日這幅圖不适合。這一道疤其實很是整齊——長刀筆直地看下來,沒有絲毫停頓。
但是因為男人身上所帶有的肌肉紋理,這道本該平滑的線條又有些彎曲。
沈嬌幾乎是一瞬間就有了靈感,于是幹脆地推翻了自己之前在腦海中構思的畫面,改做了一幅山水。
“夫君先前教導了我一句話。”沈嬌突然想到了什麼,“要主帥親身上場殺個你死我活的,不是疏忽大意落入圈套,就是兩方确實勢均力敵到了關鍵時刻。”
小姑娘嘴上複述着衛鶴景先前說過的話,手上的動作卻依舊不見停歇:“夫君受了這麼重的傷,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呢?當時是個怎樣的情景呢?”
這道疤痕一看就是要命的東西。一般人像這麼挨上一刀,恐怕早就一命嗚呼了。
她實在難以想象,究竟是怎樣的情景,才能讓這具強健身體的主人陷入生死危機呢?
而且,這麼重的傷,衛鶴景就是再怎麼強悍,應該也得暈上個十天半個月的。她此前雖然并不關心朝堂政事,但是衛鶴景是皇家血脈,一向在民間也有聲望。他受了傷這種事情,怎麼想也該在京城裡流傳一些小道消息。
但是她從來都沒有聽說過。
沈嬌開口說話,問出的問題得以讓一直辛苦抑制自己的衛鶴景稍稍轉移一些注意力。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衛鶴景微微眯起眼睛,遠處的燭光在他的視線裡化作一個個昏黃的光斑,讓他想到那個傍晚的夕陽,“那時我剛到雲州不久,邊境也不像是現在這般安穩,外頭那群蠻子時常越境偷襲。”
“我才到軍中不久,雖說手裡頭拿着帥印,可是不少老資曆都不服氣我。覺得,半大小子,不堪重任。我那時候的名聲,基本都是關于才學的,雖然好,但是在戰場上不看這個。他們懷疑我的能力,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請勿開啟浏覽器閱讀模式,否則将導緻章節内容缺失及無法閱讀下一章。
相鄰推薦:病弱美人靠沙雕觸發修羅場 穿成未來霸總他親媽 傅總今天有名分了嗎?[重生] 偏執男配隻想要我(快穿) 白月光總想無情證道 京味文小茶爺和豪門霸總HE了 山中道蓮 先知女友對上精神病男友 特别偏愛 軟話 滿級大佬穿書後爆紅全網 套路不成反被撩 赤漠遙 七零之懶人有懶福 金絲雀離開以後(ABO)+番外 白月光才不稀罕渣男們呢 如何在移民飛船上吃到菠蘿包 暫停心動 師父,我隻是一隻小老虎啊[穿書] 七零之如花美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