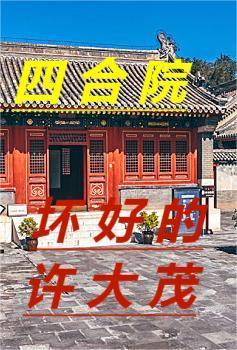書本網>攻略青樓樂師的那些年 > 第53頁(第1頁)
第53頁(第1頁)
當然了,我甯願相信他還是個正常的男人,這一切都源自于他妻子的調教。他妻子對他的調教總是随時随地給我驚喜。默了片刻,我慢吞吞地将針線包給他塞回腰間。在他炯炯的目光下,我眼也不眨地望着他,字斟句酌後措好了辭,“……挺好的。”上天,我就隻能措出這個水平的辭了嗎。是否好歹多客套一句“黛青顔色的線更好看”雲雲。他錯愕地凝視着我,似是沒有料到我看到針線包後會是這個反應。我也料不到他為何在我作出反應後錯愕。好像他攜帶針線包是什麼理所應當的事情一樣。順利地摸出火折子,酸秀才沒有推脫,隻是看我與他的眼神像是欲言又止。最終也隻是淡笑着說了一句,“順心走。”他當年,應當是沒有順心走。沉默地走在雪中,他撐起從酸秀才那裡拿走的花傘,遮住綿綿絮雪,與我并肩。我其實很想問問他,他的妻子究竟是怎麼做到的,讓他這樣一個當年在我險些跪地苦求下依舊不願意高擡貴手幫我縫衣的人,變成了行走的針線包。倘若可以,适當時機的時候能不能也讓我開一下眼界?畢竟我很難想象,如今心機深沉的景大人如我敏敏姐姐一般賢惠溫柔地縫補衣裳該是什麼神仙場景。我稍擡眸觑他,他此時面沉如霜。我便忍住了這個請求。此時夕陽正盛,我才覺得身體舒适些。不知覺間我們竟在酸秀才那間屋子裡待了整個下午。那樣陰暗潮濕的地方令我氣悶窒息,我卻覺得他待得十分從容。仿佛曾經也這般習慣過,或是一直這樣習慣着。他一手拎滿花生堅果,一手打着傘,我伸手想分擔一些,被他避開了。正在此時,不遠處傳來陣陣狗吠,在蒼茫的雪中顯得尤為奸惡。果然就在我們拐過牆角時看到了滴着口水龇着獠牙的它。棕黑色的毛濕哒哒地沾住雪水,它兇狠地撕咬着腳邊一塊白布。記憶裡不那麼深處的恐懼猛地被弢弢的犬吠聲勾起,我承認我現在也有些想要尿褲子。幸好當年他尿床的時候我沒有嫌棄過他,否則今日還不知道是誰笑話誰。景弦皺起眉,“别怕,我們走快些就好。”我也是這麼想的,可腿腳它正發着抖不大聽我使喚。腳腕被咬過那處隐隐有些發癢,我甚至想就地蹲下将自己蜷縮成團好好撓上一撓,撓得血肉模糊才好舒緩我心底強烈的癢意。那條狗沒有給我緩過腿腳走快些的時間,甚至沒給我蹲下的時間,嗷嗷地像是口水和獠牙在叫,和着大雪一起朝我沖來。它朝我瘋跑過來那刻,我驚慌呼救,隻敢抓起地上的雪團拼命打它。我怕不是天生一副招狗體質,想來上輩子應當十惡不赦,今生才落得個被狗追着咬的下場!當我眼前晃過棕黑色的狗影時,我的人已經跌坐在地上,那條狗咬住我的衣袖後不知怎麼就在半空中拐了彎。我拼命扯出衣袖将自己團縮在一起,蹬着腿向後疾退。耳邊是窸窣的顆粒掉落聲。刀光折了下我的眼,瞬間埋入吠犬的口中。我伸掌向後一撐,被手壓住的花生也驚得我渾身一抖。生怕身後還有一隻狗!趕忙回頭看了一眼!沒有、沒有……幸好沒有。花神娘娘還是很仗義的,隔幾年來那麼一條磨練磨練我的心智就好。不知道是不是我聽錯,一聲慘烈的嗚咽和着雪風砸向我。當我再次轉頭看過去時,景弦的手臂已成血紅。他的手穿進吠犬的口,那把刀的刀尖從野狗的頸背穿出來。第一刀斃命。他抽出手後又利落地割斷了它的咽喉,沒有絲毫猶豫,我卻不知是為了什麼。血水浸透他素白的袖,也流淌在雪地中,格外鮮豔。“有沒有傷到哪裡?”他将匕首插在雪中,蹲身在我面前急問。我搖頭,直愣愣地盯緊被分割的野狗。腦子裡威風的記憶好似被換洗了一番。雪中鮮紅的确比記憶中的灰雨濕地更令人印象深刻。好半晌,我才轉圜視線,垂眸看着他的手臂,“你……”“我也沒受傷。”他擡起我的手臂,我痛得一驚,原是那晚被包紮的割傷裂開了,滲出血意。袖子的縫角處也被咬開了線。這件衣裙還是六年前随容先生離開時她贈我的,意義重大。當然,我的确也為我的買不起新衣裳的貧窮尋了個合理的解釋。唯有回去換上僅有的一件換洗衣裳,将這件認認真真地縫補牢實可解我無衣可穿的尴尬。不做乞丐六年,我再次體驗到了沒錢寸步難行的感覺。“你還有換洗的衣裳嗎?”他一邊撿灑落的堅果,一邊問我。我笃定點頭,“有一件。”他微蹙起眉,我料他險些就要将“為何慘成這樣”脫口而出,硬生生憋下了,待撿完堅果才對我道,“我那裡剛好有幾件,明日給你送來。”剛好?他在說什麼?他在雲安的府邸裡存着女裝?他放置女裝做什麼?不,我不能這麼想。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直很男人的。我應笃定是他夫人的,否則按照我的想法來的話,未免太過驚悚。“我第一個月的銀子尚且沒有拿到手,你好歹等我還上一點,讓我心裡有個安慰之後再讓我繼續燒錢欠債。否則,”我抓着頭發,費解道,“我入、入不敷出啊。”他愣了愣,沉吟了會兒後對我道,“其實我覺得,沒多大差别。以你目前的月銀,就算還我一點,和十萬兩比起來,心裡仍舊很難有安慰。不過你要是覺得會安慰些,那便依你。”“……”我很感謝他。“不過,你這件衣裳得趕緊縫補好。不然沒得穿了。”他拎起堅果,撿起傘,示意我跟着他走。我想到他腰間的針線包,其實不太好開口問他借的。我怕說出來會傷他的自尊心。可當我們回到教讀的書房後,他主動拿了出來。并讓我選個顔色。與他真摯的眼神銜接片刻,我選了銀白,“你先出去罷,我脫下來自己縫。你的針我也借用一下。”他接過銀白的線,淡然問,“你的女紅不是不好嗎?”難道你一個大男人的女紅就很好嗎?我盯了他片刻,低頭道,“現在還可以。”“這麼冷的天,便不必脫了,省得麻煩。”他拈起我的袖子打量片刻,“隻是斷了幾根線,破得不多,十針之内。我幫你縫了便是。”他說的話竟有些許專業。我以為這幾年應當是他妻子在外打拼,而他在家裡打理内務。這麼一想我竟覺得他妻子至今未歸這件事就說得通了。我究竟是個什麼魔鬼。怔愣之間,他已在我身旁蹲下,微虛着眸子觑那針孔。又将銀線穿過那針孔。打上結。翻過我的袖子,手起刀落般地快準穩。他縫補得未免太過專業。六年不見,他愈發富有神秘氣息。我知道,我此時看他的眼神一定撲朔迷離。幾乎隻在我幾個眨眼間,他已将我的袖子補得漂漂亮亮的。而他還擡起眸來沖我笑。娴熟得令人心疼。我捏着袖子,遲疑地道謝。尚沉浸在連篇的臆想之中,忽聽他在我身旁輕聲問,“記憶深刻否?”我微皺了下眉,不解地望着他。他的眸底一如酸秀才的房間那般陰冷潮濕,是我窺視不了的深淵,亦使我胸悶氣短。他一邊收拾針線,一邊在指尖摩挲輕拈,翹起的嘴角像是方才那把刀頭微勾的匕首,後來沾了血的模樣,“那隻野狗的死狀,給你留下的記憶深刻否?”我一怔,他的聲音不容置疑,我亦照實點頭。雪地的白,匕首的白,素衣的白,都襯得鮮血極紅。像瞠目直視豔陽般烙印在腦海。可他事後的關切又讓我覺得并不可怕。我想,看見野狗那一瞬間我是想起了掰斷犬骨的小春燕,而如今若再看見野狗,我當先想起的是淋漓的鮮血、蒼茫的大雪,和刺穿野狗咽喉的景弦。
請勿開啟浏覽器閱讀模式,否則将導緻章節内容缺失及無法閱讀下一章。
相鄰推薦:異能者穿越年代後的悠閑生活 合租情緣 被反派鳏夫盯上了(女尊) 海底兩萬裡同人碎片+番外 蠱毒 家連+番外 雨族 我在馬甲文裡抱大腿發瘋 痛酒狂詩少年,劍道人間紅顔 郎君一抱好歡喜 就等你下課了 進擊的菜籽 盜墓鬼手 龍之狷狂 冷月 會變的顧醫生 拐個大王做夫君 死神:瀞靈廷的自律隊長 撩到那個男人[快穿]/他從黑暗中走來 (綜漫同人)一夢一渣+番外